请登录查看大图。42+万用户选择下载看福清App享受全功能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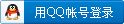 |
|
x
上世纪50年代末,中国经历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,笔者还是个十岁出头的毛头孩子,住在福清乡下积库村。记忆里,那几年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,风里带着尘土和野草的味道。 福清地处东南沿海,田少地瘠。那几年,集体化生产遭遇严重挫折,加上自然灾害,粮食产量锐减。每到饭点,端到生产队饭桌上的,几乎都是几块地瓜片清汤,或者能够照出人影的稀粥,外加一盘清煮包菜。 面对这样的宭境,县里开始倡导农民利用荒山、荒地、田埂的边角地开荒种地,以补充口粮。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政策松动。因为公社化时,土地全部归到集体所有,私自种植会被批评甚至处分。但在粮食紧缺的压力下,上级不得不调整政策,允许农民开垦闲置山地,种上自家需要的粮食和蔬菜。 (二) 记得听到消息的那天,父亲沉默了很久,然后对我们说:“明天开始,全家都去山上。” 那时没有农耕机械,全靠锄头、洋镐、镰刀和双手。天刚蒙蒙亮,我们就扛着工具,带着水壶和为数不多的干粮上山。
父亲负责挖地。母亲和笔者则捡石头、清理杂草。弟妹年纪尚小,就把挖出来的土块敲碎。积库村的山坡多沙石,土层薄,一洋镐下去,不是碰到石头就是草根盘结。父亲的手掌很快磨出了水泡,水泡破了,渗了出血,和泥土混在一起,双手火辣辣地疼。父亲却总是笑笑,说:“做田人,靠的就是这股‘牛力’。” 中午,我们只在山坡上啃几口“麦粕饼”,喝几口凉白开。傍晚回家时,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 最初几天,我们只开出一小块地。父亲说,别急,地是一寸一寸开出来的。就这样,我们连续干了一个多月,终于开出了几分能种庄稼的坡地。
(三) 那年春天,父亲在新开的地里种下了耐旱的番薯,还种了黄豆。后来又在田埂边播下了南瓜籽,因为南瓜产量高,既能当菜吃,在夏秋之交青黄不接的时期,又可以瓜代粮。 夏天来了,山坡上一片绿油油的。番薯藤蔓爬满了坡地,黄豆长出了饱满的豆荚,南瓜开出金灿灿的花朵。我们常常来到地里除草、施农家肥、浇水,汗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,咸咸的。父亲看着这些庄稼,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:“今年,至少饿不死了。”
第一年秋天,收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。母亲用番薯制作出各种食物——番薯粥、番薯饼、番薯粉、番薯干,甚至还摘下鲜嫩的番薯叶炒成菜。虽然依旧没有白米饭,但饭桌上多了颜色和香气,家里的笑声也多起来了。 (四) 回望那段岁月,依靠自力更生,我们度过了荒年,尽管异常艰苦,心里却不由地生起一种踏实感。因为我们知道,地里长出来的每一颗粮食,都是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。它不仅添贴了家庭的粮食不足,更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希望。 如今,一个甲子过去,福清早已发生了沧桑巨变。高楼林立,道路纵横,一家一户的食柜中、冰箱里,食物种类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。每当看到餐桌上的番薯、豆腐,我们总会忆起那个在山坡上挥汗如雨的岁月,忆起父亲紧握锄头柄的背影,想起一家人风雨同舟苦度的日子。
via知福清 作者:薛守维
|